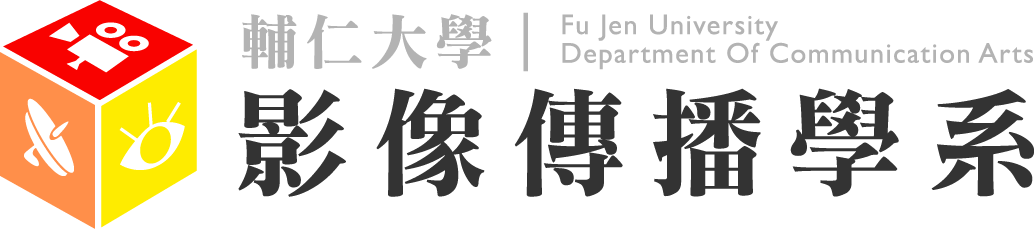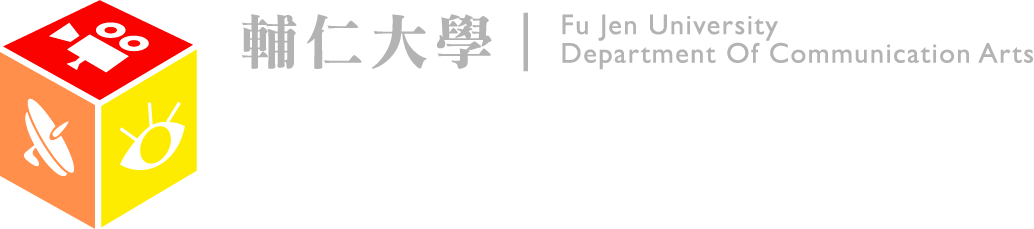輔大傳播學院三樓攝影棚外,期末考週常常嘈雜無比,多次干擾引起其他教室上課的師生抗議。這時,攝影棚內響起:
「輔大第一屆迷你金鐘獎,開~始~…」
(音樂)
副控室內的導播下指令:
「片頭10秒倒數,10,9,8,7… CAM1 dolly in 3秒 take Cam2 主持人說話…」
「這是輔大第一次舉辦迷你金鐘獎,背後的…」男主持人西裝筆挺,女主持人正式套裝,全部帶妝粉墨登場。
現場FD倒數,帶動觀眾掌聲響起…音效、燈光、場地都設計過。
這是輔大影傳系大一的必修課「廣電概論」期末考試現場,迷你金鐘獎頒獎不能NG的全程轉播。經過一學期教學的成果,轉播過程順暢,但製作前的過程並不簡單。
大一新生的同學,聽到學期開始授課的黃老師宣布期末的要求,好像都事不關己,課堂上沒有太多意見。課後,大一生事後跟老師反映:「轉播迷你金鐘獎喔?老師,我們甚麼都不會耶?」黃老師回說:「會了,就不用來了」然後一片茫然。
這是一個化不可能為可能的任務,挑戰大一入門的學生,讓他們動起來上課,而非像高中一樣坐在教室聽講。大一確實還在摸索,授課的黃老師思索如何讓他們直接用問題為導向的教學法、師徒制、自主學習法來教。這只是一門影傳系大一新生必修的「廣電概論」,有別於以往課程設計,是一項新的嘗試。
任課的黃老師想著變花樣,翻轉教學,教授全體新生分組製作各類型的廣播、電視影片,學習提出企劃、進行拍攝製作出作品,再由老師進行審查評比,利用做中學,學習和印證廣電概論的各種現象和理論,「坐而言不如起而行,新生應該會印象深刻,學到入門的知識和概念,為以後深入的課程打下基礎。」
經過醞釀,有企劃案提出了,被老師批說「你做不到」,果然這組終於知道廣電管理與製作,需要懂製作,也要評估資源、能力、時間、還有觀眾收視的習慣。上課強調廣播的命脈是聲音,聲音是魔術師,是吃飯的傢伙很重要,多重要?不知道,做出來才知道,啊,丟三落四、漂浮不實、內容鬆散,回去「認真去聽廣播,做廣播」。電視影片組用台大割頸事件當教材,演出來,當作學習教材,學習製作新聞報導,SNG轉播即時新聞,其實骨子裡在教台灣的廣電新聞生態,一起批評一起提出改善策略。好吧,那就做出不要腥羶色的新聞,有同學提出製作校園聖誕點燈,應該畫面美氣氛佳,但是鏡頭不會操控,影像概念沒有、攝影機鏡頭語言粗糙,無法達到預期效果,藉此學習好的想法,也要有好的技術,才能相輔相成。
除了廣播組和電視組,全班其他成員還分成企劃組和製作組,分頭學習節目企劃、行銷、節目執行,製播人員學習棚內攝影、副控室進行直播的操作作業。分別進行教學,並請輔大電視台的學長傳授攝影棚錄製的方法,進行小組課後教學。
影傳的新生經過教學、刺激、自主學習、彼此討論,作品漸漸磨出樣子:廣播有重視老人傳播需求、青少年心聲反映、城鄉差別的議題、社區發展、當然還有流行音樂、電影娛樂的詮釋與創作。電視有兩齣校園實境秀,做得有模有樣。
問題出在協調溝通與企劃執行,因為牽一髮動全身,只有有一個人沒有做好份內的工作,比如,學錄影,有一人沒到,就無法進行。學企劃行銷,只要有人忘了交行銷影片,就玩不下去。大一同學彼此不熟,溝通管道還沒有完整建立,有的同學本位主義還根深蒂固,有的同學還停留在高中被動學習階段,不催不動,各組負責人還沒有學到領導統御,如何說服別人合作不到位,因此各組負責人吃足了苦頭,常常熬夜守在桌前,等別人從電腦的一端繳交作品上雲端,學期最後一兩周,密集彩排迷你金鐘獎,一天睡不到三小時,火氣大,長針眼。怪老師,教學沒有層次,要求不清楚。「老師,我說真話,不怕你當我」,情緒已經快爆炸了。
但是,黃老師不但沒有當他,虛心接受,還給他很高分。老師要磨同學的,其實是在課堂外的討論、溝通、學習尊重、製作、團隊合作,本意在設下迷你金鐘獎的情境,讓同學一步一步地克服困難,完成作品,這和課堂裡的反覆教授理論、方法、記憶理論、模擬技藝,同樣重要。因為在業界,不會有人反覆提醒你:該做這,該做那。命令一下,就要想方設法完成,過程有困難一定要及時提出討論,不能拖,等到驗收了才提問就晚了,而這都是在學校要學習的。輔大影傳系利用各種資源,讓他們一步一步地學習和完成。
結果,課程結束了,轉播完成。大二下修的同學寫下心得是:「說真的,大二來做都很吃力,沒想到大一竟然完成了」。(黃乃琦老師撰稿)